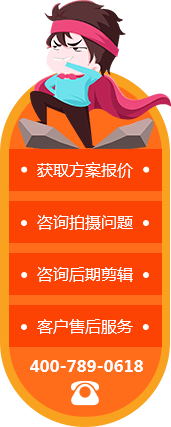利·柯比1961年根据杜拉斯《长别离》改编的同名电影中,黛莱丝坚持认为一个每天路过自己咖啡馆门口的流浪汉是自己在战争中失踪的丈夫,她试图让他恢复记忆。
这是这部电影最“杜拉斯”的片段,重复与迭词构成的线年等待的焦灼和相逢并不能相认的痛苦。作为编剧之一的杜拉斯对柯比用大量沉默场景和象征手法拍摄这部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电影很不满意
.jpg)
(1944年罗贝尔·安泰尔姆被德军俘虏,作为妻子的杜拉斯多年营救的努力也只能换来战争结束后才归来的已经奄奄一息的丈夫)。
在杜拉斯这段传奇电影生涯的尾声,1980年,《电影手册》策划出版了一期杜拉斯的特刊,之后以《绿眼睛》的名字发行,收录了杜拉斯的随笔、札记和访谈,其中有杜拉斯看似随意的只言片语,也有深思熟虑的思考凝结的论述。有与电影创作者的有趣对话,也有写意的摄影图片。
《绿眼睛》这个名字也直观表达出杜拉斯希望通过这部文集来表达自己对于错综复杂的观念与现实世界中的探寻。
.jpg)
在《绿眼睛》出版的当年,66岁的杜拉斯开始了与27岁杨·安德烈相爱,因此《绿眼睛》中众多的少女摄影似乎也有杜拉斯自我的身份指认。
《绿眼睛》就像是一次时光之旅,短视频制作也是一份邀请函,邀请你进入一位具有深刻影响力的艺术家独特而感伤的世界。
整部书虽然也是杜拉斯一贯的零碎与直接,成都短视频拍摄但其中不乏灵光乍现的真知灼见和横跨多个艺术领域的批判见解。
杜拉斯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恶,虽然她在《电影手册》早期与同样推崇文学的“左岸派”们走的很近,以至于很多人简单地将杜拉斯也划归于“左岸派”,但杜拉斯本人对“左岸派”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反而对“手册派”的代表人物戈达尔推崇备至。
在与美国著名导演伊利亚·卡赞的对话中,大部分的时间杜拉斯都在谈卡赞的夫人芭芭拉·洛登在1970年仅花费15万美元拍摄的独立电影《旺达》,杜拉斯敏锐地发现了这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电影中强烈的女性情感表达和自我意识的凸显,粗颗粒的画面和对传统电影情节的解构都让《旺达》符合杜拉斯
要理解杜拉斯独特的电影观,书中的那些看似“出言不逊”的文字是一条捷径。在《做电影》中,杜拉斯对“作者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认为电影创作者越来越变为了对影像的一种机械的复制者,害怕票房的失败和评论的压力,“作者”向制片商、观众妥协,已经失去了面对自我的责任感。
,所以她不喜欢同样为作家转型导演的阿兰·罗伯-格里耶,也许在杜拉斯看来,格里耶的无序与松散的意识流是通过影像而非文字在传达意义。
杜拉斯希望“创造一种万能图像,可以无限地与一系列文本叠合”并且“只有当文本穿越过它时,意义才随之产生”,
而1975年杜拉斯最伟大的电影作品《印度之歌》的出现就完美印证了杜拉斯的理论。《绿眼睛》中杜拉斯本人也将《印度之歌》看作是自己的电影代表作,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杜拉斯甚至说,她只拍过一部电影,就是《印度之歌》。
在《印度之歌》中,印度这个殖民地成为了身份本身的“漂浮”的存在,就如杜拉斯在湄公河畔度过的那些自由又忧伤的童年时光,作为“下等白人”的杜拉斯在《印度之歌》中描写了上层与下层阶级的两个女人的命运,但不管是大使夫人还是女乞丐,她们都难以逃离死亡的宿命。
,让观众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声音上,因为声音才是左右这部电影的主人,画面只是一些片段式的回忆和对声音的补充。
咏叹调的歌剧、海浪和鸟叫等自然音、断断续续的对白和达莱西奥·弗斯克荡气回肠的配乐交织着,声画错位的套层结构中,加尔各答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饥饿、疾病和焚尸炉,浪漫奢华的上流社会的舞会的画外音却是大使夫人精神上的痛苦,她感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死亡,宏大的时间流逝和个人瞬间的消逝。
杜拉斯让时间与回忆的战争变得如此痛苦,精神上的沉思和形式上的松散融为一体,她告诉观众命定的结局,让她的角色置身于一个没有人性的物质世界
,没有任何超脱的希望,并让回忆的痛苦被静态的沉稳的构图消磨掉时间的痕迹,只剩下梦游后的叹息。
我们会想到《长别离》中黛莱丝在与流浪汉跳舞时发现流浪汉头上的伤痕,这同样也是时间与回忆的共谋,这个场景仿佛是一个穿越过去的时间胶囊,黛莱丝哭了,但短暂的绝望后,她继续问道
《她威尼斯的名字在荒凉的加尔各答》中没有人物,只有演员的声音,而《卡车》里热拉尔·德帕迪约饰演的卡车司机与杜拉斯本人饰演的中年妇女在窗帘紧闭的屋子里念剧本。
在这些极端的实验中,影像的空间被完全改变了,空间开始变得“不可视”,开始变成需要观众去想象,需要通过对白构建的客体,
杜拉斯由此解放了电影中画面影像的束缚,让电影变得文学化,也让文学获得了多重的复调叙事的可能。
借由摄像机的客观性和文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未经过滤的现实与精心制作的叙述之间的复杂互动,杜拉斯用这种纪录片与自传的影像结合的探究,表达着她个人旅程中的感人一瞥,也是对
《绿眼睛》不仅仅是一部有关于杜拉斯电影创作的文集,其中也包含了杜拉斯在经历60、70年代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和狂飙突进的文艺后对生活、艺术、情感的感受。
杜拉斯很长时间里被看作是一个通俗的流行文学作者,她直到70岁发表《情人》后才得到了龚古尔奖,而与杜拉斯销量巨大的小说相比,其电影却曲高和寡,票房惨淡,
,在“逃离”写作的那些年里,杜拉斯也没有质疑过这一点,杜拉斯的小说与电影从来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杜拉斯的“绿眼睛”还是她手下笔的延伸。
对于杜拉斯来说,原点就是11岁时的湄公河,燥热的湿气掩盖了翠绿的椰林,赤脚奔跑时脚底传来的刺痛感
而这本《绿眼睛》、这些电影,它们证明了一个艺术家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哪怕直到海角天涯。